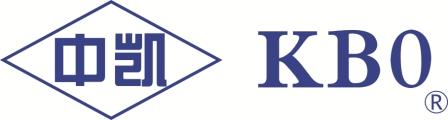- 業界中國風電 穿越技術無人區!2023-02-21 來源:網絡綜合 | 點擊率:導語最新的海上風電機型被國外市場認可,率先在海外投運,這是前所未有的。中國風能人付諸多年心血推動的“兩海”戰略正在形成合圍之勢,或許將創造風電歷史的另一個里程碑。
中國風電已經發展成為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主力能源,是支持電力系統率先脫碳,進而推動能源系統和全社會實現碳中和的“主力軍”。到2022年11月,中國風電不僅在累計并網裝機容量上達到了3.5億千瓦,連續十余年穩居世界首位,還在風電機組的研發與制造上取得重大突破,金風科技GWH252-16MW、中國海裝H260-18MW、明陽智能MySE18.X-28X和MySE16.X-260等單機容量達16~18MW的大型海上風電機組接連下線與發布。
看似朝夕間的質變,卻是幾代人的拼搏成果。當多方有利因素通過一代代風能人的手聚沙成塔,所迸發的力量銳不可當。
“我們正在邁入風電技術的‘無人區’,未來充滿挑戰,卻創造更多可能。”一位專注于解決未來風電技術難題的專家對《風能》談道。
看得見的未來
是什么推動中國風電技術迎頭趕上了國際同行呢?這與發展規劃、電價政策、技術進步、產業配套等多方面的有力支撐息息相關。其中,最關鍵的是發展規劃為中國風電創造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未來。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
結合上述目標,國家進一步明確到2030年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12億千瓦以上,對風電發展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
為落實國家大政方針,風電行業通過科學推算、自發組織,先后兩次發布含有明確發展目標的宣言與倡議。
在2020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CWP 2020)上發布的《風能北京宣言》中提到,為達到與碳中和目標實現起步銜接的目的,在“十四五”規劃中,須為風電設定與碳中和國家戰略相適應的發展空間:保證年均新增裝機5000萬千瓦以上。更遠期,2025年后,中國風電年均新增裝機容量應不低于6000萬千瓦,到2030年總裝機容量至少達到8億千瓦,到2060年至少達到30億千瓦。
不久前發布的《2022全球海上風電大會倡議》提出:綜合當前發展條件以及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要求,到“十四五”末,我國海上風電累計裝機容量需達到1億千瓦以上,到2030年累計達2億千瓦以上,到2050年累計不少于10億千瓦。
據不完全統計,在積極且穩定的頂層設計和“1+N”政策的持續引導下,僅各地出臺的海上風電規劃總容量就已超過8000萬千瓦。
2022年,歐洲能源供應問題警醒各國,能源安全成為焦點。就此,風電已不僅僅因其綠色與市場價值在能源體系中發揮作用,更將成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的關鍵組成部分。
“值得強調的是,可再生能源是本國可以掌控的、不受國際地緣政治變化影響的能源。隨著非化石能源比例的增大,它在能源供給安全中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撰文表示。
作為推進碳減排與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舉措,我國風電躍升發展實屬必然。在如此有利的客觀環境下,風電技術領域不僅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各類資源與資金也正在此匯集,形成推動風電技術發展的澎湃動力。
滿足市場化需要
積極的政策引導與可觀的發展預期,創造了巨大市場空間。同時,風電平價與競價政策的落地,又對開發收益產生較大影響。
2019年5月2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完善風電上網電價政策的通知》(發改價格〔2019〕882號)明確規定,2018年年底之前核準的陸上風電項目,2020年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網的,國家不再補貼;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年底前核準的陸上風電項目,2021年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網的,國家不再補貼。自2021年1月1日開始,新核準的陸上風電項目全面實現平價上網,國家不再補貼。將海上風電標桿上網電價改為指導價,新核準海上風電項目全部通過競爭方式確定上網電價。對2018年年底前已核準的海上風電項目,如在2021年年底前全部機組完成并網的,執行核準時的上網電價;2022年及以后全部機組完成并網的,執行并網年份的指導價。
“一方面是大規模發展,一方面是市場化的電價對項目的收益預期產生影響,這要求開發企業更膽大心細。”風電開發技術專家張輝認為:“為做到規模與收益的兩者兼顧,在開發模式和風電技術上發力是最佳途徑。”
風電項目開發降本的途徑有很多,包括規模降本、管理降本、工程降本、技術降本等。在開發模式上進行創新,主要是有利于規模與管理降本。行業專家一直建議地方政府將項目規模設置得足夠大,以攤薄項目開發乃至區域產業發展的整體成本。而在風電技術方面,目前最行之有效且普遍采用的方式,是通過提高機組單機容量,降低機組的單位千瓦造價。
“從風電機組研發的本身而言,近些年降低風電項目開發度電成本的主流技術途徑,是在確保機組發電能力前提下的大型化。”張輝認為。
中國海裝研究院機械設計所所長、H260-18MW產品負責人楊微,以中國海裝H260-18MW為例解釋機組大型化滿足風電開發降本的邏輯:“它具有全球最大風輪直徑,在相同條件下能夠吸收更多風能、發更多的電;同時,更大功率提升發電量的同時,可以有效節約用海面積、降低機位點數量,進而降低海上風電場工程建設與運維成本。”
因此,機組大型化帶動的不僅僅是技術降本,更重要的是對工程降本有利。這在機組設備成本占比較低的海上風電市場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以100萬千瓦的海上項目測算,相比10MW機型,18MW機組所需機位點更少,工程施工成本更低,工程單位千瓦總投資成本可降低20%以上,施工時間窗口可減少30%以上。
致力于做得更大
說到大,主流的海上風電機組幾乎比陸上機型大一倍,這正是由海上風電工程成本高、施工與運輸條件所決定的。據《風能》統計,2022年我國下線的海上機組最大單機容量提高了7MW之多,這幾乎是一臺陸上新型機組的單機容量。
據了解,我國海上機型共經歷了三代發展。第一代產品是通過整機引進或在歐洲知名設計公司的指導下,結合我國海上復雜環境研發出來的,風輪直徑小于150m,單機容量小于5MW。第二代產品開始自主研發,單機容量不超過8MW,風輪直徑小于200m,是“搶裝”時期的主力機型。第三代產品是以平價為特征的8.5~16MW機型,風輪直徑達到200~260m,一些產品具有較強的抗臺風能力。
在新產品的研發過程中,為保證發電能力,單機容量越大風輪直徑也需要相應地增大。各部件重量與載荷的增加,使技術難度大幅提升,研發人員必須突破更多瓶頸。
“機組的大型化,不是簡單的延伸和放大。隨著功率、載荷的增大,零部件的尺寸和重量將急劇增加,如果不通過基礎技術創新拓展大型化邊界,超大容量機型開發就不具備可行性與經濟性。”楊微對這一點頗有感觸。
因此,越來越多的整機企業將目光轉移到中速永磁(也稱半直驅、混合)技術路線上。在2022年,新下線的海上風電機型共12款,其中有10款采用了該技術路線。
“中速永磁技術實現了重量、可靠性、成本等多方面的平衡,從而可以做到更大。”張輝解釋。
當然,除了技術路線外,我國風電整機技術還有諸多方面實現了突破。例如,深遠海大功率風電機組整機支撐結構一體化設計技術,整機平臺化設計技術,智能控制技術,大功率整機與超長葉片仿真測試驗證能力等。
以深遠海大功率風電機組整機支撐結構一體化設計技術為例,通過對風、浪、海床等外部條件以及主機、塔筒、基礎等結構的一體化建模,并在高速迭代能力支持下,可實現葉片、機艙結構件、塔筒與基礎等的輕量化設計。“在此過程中,全耦合的一體化建模,以及一體化全耦合模型的求解解耦是具有相當難度的,我們必須迎難而上。”楊微談道。
越來越大的風電機組不僅考驗整機研發人員的能力,也同樣考驗著我國風電工程技術水平。值得慶幸的是,“基建狂魔”深諳此道。
據了解,中國海裝首臺H260-18MW機組計劃安裝的浙江蒼南項目,離岸50km以上,水深30m左右,是全球最極端的臺風頻發海域。且該項目海底有比較深的淤泥,施工挑戰大,具有典型的深遠海風電場開發特征。
“受制于海上機組吊裝對吊高和樁腿長度的技術要求,目前國內滿足18MW機型安裝要求的安裝平臺有1艘,但2023年將有3艘新一代自升式風電安裝平臺服役,未來5年預計將有10~20艘具備該級別海上機組吊裝能力的風電安裝平臺。”楊微稱。
關鍵部件發力
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速永磁技術路線,避開了一些其他技術路線機型實現進一步大型化的難點,尤其是給一些關鍵零部件的大型化創造了有利條件,也更易發揮出我國在風電關鍵零部件方面的產業優勢。
“雙饋發電機的大型化難點在于轉速高引起的轉子線圈及轉子組件的結構可靠性,對轉子的動平衡精度及滑環可靠性要求很高;直驅發電機轉速低、體積大、重量重,大功率化后裝配、浸漆、吊運等都難以實現,對設備及工裝的要求極高,而且受永磁材料成本影響,單機成本也非常高。”楊微談道:“超大型中速永磁發電機,巧妙地避開了雙饋與直驅的設計難點和制造痛點。”
中國海裝提供的數據顯示,該公司為匹配H260-18MW機型下線的19MW中速永磁發電機外徑3.4m,重量僅為33t,兩項數據都比1.5MW的直驅發電機小。
然而,這并不代表企業在研發中速永磁發電機過程中,沒有提升技術水平。事實上,為了使中速永磁發電機更緊湊,研發人員正在不斷提升其功率與轉矩密度。以H260-18MW機型為例,其功率密度高達350W/kg,轉矩密度不低于12kNm/t。
齒輪箱也是同樣的道理。據介紹,高速傳動鏈齒輪箱扭矩密度目前能達到140Nm/kg,如果不通過技術創新提升其扭矩密度,18MW級風電機組僅齒輪箱重量將達到約160t。
“在由發電機與齒輪箱所組成的發電單元中,齒輪箱的重量占到三分之二,優化它的意義更大。”在進一步談及中速傳動機組的大型化發展時,張輝認為多行星級、多行星輪及傳動鏈高度集成化,是提升傳動系統扭矩密度的關鍵:“齒輪箱行星輪數量越多,能夠分擔的總功率就越大,在同樣功率下齒輪箱重量就越輕。”
據楊微介紹,中國海裝H260-18MW機型正是通過采用多行星級、多行星輪技術,將齒輪箱扭矩密度提升到210Nm/kg,這可視為全球先進水平。
相比發電機與齒輪箱而言,葉片更可能成為機組大型化的卡點。為突破葉片長度極限,中國葉片廠商不斷革新生產工藝,嘗試高性能材料,優化氣動設計。仍以中國海裝H260-18MW機型為例:在設計上,嘗試了適用于復雜環境的高雷諾數風電機組葉片翼型氣動設計、超長柔性葉片氣動―結構―載荷一體化設計等技術;在材料上,其選用了高模玻纖、碳纖維、聚氨酯等;在生產工藝上,采用國產大絲束碳纖維拉擠板整體成型、自動化鋪層與葉根及尾緣梁預制成型、超長葉片殼體一體灌注成型、多腹板組裝及合模智能裝配、相控陣無損檢測等先進技術,確保葉片從設計、材料、生產、檢測到運行全生命周期的可靠性與穩定性。
新賽道開啟
不久前,中國海裝對外宣布,將繼續研制300m以上風輪直徑、25MW以上輸出功率的機型。風電機組到底能做到多大,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各關鍵零部件,而在目前技術條件下,后者的大型化技術邊際不盡相同。
“單機容量持續增大后,發電機定轉子體積重量增大,集成式結構發電機重量由齒輪箱承重,功率增大帶來軸向和徑向方向變長變大,轉子撓度不足影響氣隙,進而影響發電機效率和發電性能。”楊微推測:“結合目前新技術新材料的研發進度、行業供應鏈成熟度、設備加工制造能力等因素,初步預估現有的常規水平軸風電機組瓶頸在30MW級左右。”
相比發電機來說,葉片的提升更難。這是因為葉片長度的增長不僅取決于技術,同樣還要求生產廠房不斷改建,投入更多配套生產工裝,也受制于運輸和吊裝難度。楊微認為,葉片長度的發展會更快達到瓶頸期,預計將有一段時間停滯在130m級,直至在材料或工藝上取得新的突破。
當中國風電技術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就意味著在未來發展進步過程中,要越來越多地依賴自身能力的提升。
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我國對海上漂浮式風電技術的探索,正小步快跑地進行。在這個領域,可借鑒的國際經驗也并不豐富。與固定式風電有所不同,漂浮式風電機組必須搭載更先進的控制技術,掌握浮體運動控制策略,使機組能適應風、浪、流等復雜運行環境。
為了抓住這把解鎖深遠海風電規模化開發的“鑰匙”,中國已經有3家整機商與開發企業、工程技術單位展開深度合作,下線了4款漂浮式風電機型。其中,有2款機型已經在廣東海域安裝與并網,1款機型計劃2023年在設計水深200m、離岸距離10km的挪威海域投運。
最新的海上風電機型被國外市場認可,率先在海外投運,這是前所未有的。中國風能人付諸多年心血推動的“兩海”戰略正在形成合圍之勢,或許將創造風電歷史的另一個里程碑。






電廠關鍵技術研究及其應用”專題征稿通知.jpg)